在互联网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直播行业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已经成为大众娱乐和社交活动的核心平台。直播打赏作为主播获取收益的关键方式,在人们的网络生活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然而,随着直播打赏的普及,相关的法律纠纷也日益增多,因此,明确直播打赏行为的法律属性以及探讨撤销权的适用情形显得尤为关键。

一、直播打赏行为的法律性质之争
(一)关于赠与合同的观点
主张赠与合同的观点认为,打赏行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百五十七条所规定的赠与合同特征相吻合。在直播平台上,主播进行表演,观众可免费观看,打赏完全基于观众的自愿,属于无偿的财产转移,从而在打赏人与主播之间形成了赠与合同的法律关系。例如,在展示才艺的直播中,观众因欣赏主播的才艺表演,如歌唱、舞蹈等,出于喜爱和赞赏而自愿打赏,这表明打赏人与主播之间不存在强制性的对价关系,符合赠与行为的单务性与无偿性特征。从赠与人的角度出发,必须自愿表达将其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的意愿;从受赠人的角度出发,则需表达愿意接受该财产的意愿,双方的意思表示达成一致。赠与合同作为诺成合同,其成立基于意思表示的一致性,《民法典》第六百五十七条并未明确指出赠与合同需要交付财产。
(二)关于消费合同的观点
消费合同的观点则从直播的模式、交易方式以及主播获取报酬的来源等多个角度对直播行为进行分析。从直播模式来看,主播通过网络平台进行表演,观众购买主播的表演服务,形成了非强制性的付费服务合同法律关系。从交易方式上,打赏人通过网络交易平台充值并兑换虚拟货币,再用这些虚拟货币打赏主播,而主播是与直播平台结算获利,并非直接从打赏人处获得。以游戏直播为例,观众观看主播展示游戏操作技巧,打赏行为可视为对主播提供的游戏解说、互动等服务的付费。
(三)综合分析与判断
综合分析后,将直播打赏行为认定为赠与合同似乎更为妥当。一方面,主播的直播展示并非完全依照打赏人的意愿进行,因此打赏不能简单地视为对直播服务的对价支付。另一方面,打赏行为具有随意性、不确定性,金额不固定,这些特点与赠与行为的特征相符合。尽管打赏人通过网络交易平台购买虚拟货币的行为属于消费行为,但打赏人最终是通过虚拟货品在网络平台购买虚拟礼物进行打赏,这与在实体店购买商品后赠与他人并无本质区别。
二、直播打赏行为撤销权行使的情形
(一)未成年人打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其在直播平台上的打赏行为无效,监护人有权要求平台全额退款。对于八周岁以上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因其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若未经监护人同意进行的打赏行为,且该行为与未成年人的年龄、智力不相适应,监护人请求网络服务提供者返还该款项时,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
在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一名十岁男孩小州在未经母亲同意的情况下,使用其母亲的支付宝密码,向直播平台充值近两万元用于打赏主播。母亲发现后,通过平台的“未成年人误充值退款”通道申请退款,但平台以“未成年人二次打赏行为所造成的损失应由未成年人自行承担”为由拒绝退款。小州在母亲不知情的情况下,再次使用母亲账号在同一平台频繁充值、打赏,累计金额达到十四万余元。母亲再次申请退款遭拒后,将平台经营者诉至法院。法院审理后认为,小州母亲作为监护人,在第一次打赏行为发生后,未尽到对小州的监管责任,存在过错,因此酌情判决平台退还部分充值款及利息,并赔偿律师费。二审法院维持原判,认定案涉账户存在成年人混用情况,争议充值款项不能完全界定为未成年人充值,且监护人未尽到监管职责。
在四川省宜宾市珙县,一名未成年人使用绑定家长银行卡的账号向某短视频平台充值一百一十二次,共计三万余元打赏多名主播。家长报警后,珙县警方通过沟通申诉成功将三万余元的打赏费用追回。律师指出,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打赏主播的行为在法律上属于无效民事行为,平台方需将未成年人打赏主播的钱予以退还。
这些案例均表明,在未成年人打赏纠纷中,法院会综合考虑多种因素来判定款项是否应退还,同时也提醒监护人要加强对未成年人使用网络及账户的监管。
(二)夫妻共同财产打赏
夫妻一方使用夫妻共同财产进行直播打赏,若该打赏行为不属于因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合理处置,且另一方对此不知情,该行为可能被认定为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特别是当主播直播内容含有低俗信息引诱用户打赏,或者双方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时,夫妻另一方有权行使撤销权并要求返还赠与财产。
在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杨某与妻子高某共同经营餐馆,高某迷上直播后结识主播孙某,并发展到线下约会。孙某通过各种话术诱导高某在直播间疯狂打赏,九个月内高某共向孙某发送虚拟道具一万八千二百九十三次,孙某个人获得直播收益折合人民币四十五万余元。杨某发现后,以高某违背夫妻忠实义务、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为由提起诉讼,要求主播孙某返还全部收益。庭审中,双方就打赏性质产生分歧,杨某认为高某与孙某关系不正当,打赏行为违背公序良俗,应属无效;孙某则辩称打赏是娱乐消费行为,并非赠与。法院审理后认为,高某的直播打赏虽属网络服务合同中的消费行为,但其线下与孙某以恋人身份交往,突破正常互动关系,违反社会公共道德和善良风俗,且打赏数额明显高于正常网络娱乐消费水平,孙某明知高某已婚还引导其打赏也存在过错。最终,法院判决孙某十日内将其所得收益的一半二十二万余元返还杨某。
在湖北省利川市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小白(化名)作为某app用户,在直播间向多位主播赠送过礼物。小白之妻小七(化名)发现丈夫向主播小美(化名)赠送礼物金额近十万元,对此提出异议,要求小美退还全部赠款,但被拒绝,遂诉至法院。办案法官表示,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有平等处分权,小白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小美在接受打赏时,没有义务探究款项是否为小白夫妻双方的共同意思表示。小白的充值行为针对的是直播平台,充值本身并未违反公序良俗原则;打赏行为尽管针对的是小美,但打赏行为并不需要纳入法律评价;现有证据也不足以证明小白与小美之间存在其他不正当关系。最终,除四千五百元微信红包退回外,小白在直播间“打赏”的钱均不能退回。
这两个案例体现出在夫妻共同财产打赏纠纷中,法院会综合多方面因素,包括夫妻关系、打赏数额、主播与打赏人关系等进行判定。
(三)基于欺诈或重大误解
当主播存在故意隐瞒重要信息或诱导观众进行不当直播打赏行为时,法院可能认定合同无效。若打赏行为是因为重大误解而作出的,法院会认定该行为可撤销。但在此类情况下,打赏人需要提供充足的证据来证明欺诈或重大误解的情况,否则法院难以支持其诉求。
在徐州铜山法院审理的一起网络主播要求经纪公司支付直播礼物佣金的演出合同纠纷案件中,A公司为提升旗下主播李某的人气,在直播初期用不同账号为其刷礼物,营造出直播间受追捧的假象,诱导真实观众大额打赏。李某直播账号在2019年9月、10月的礼物收益显著高于其他月份,双方后续签订的协议也载明A公司为李某投入虚拟礼物现金价值七十万元。法院认为,A公司投资刷礼物的行为,目的在于暗示、诱惑或者鼓励用户大额非理性“打赏”,双方具有通谋制造虚假流量欺诈消费者的主观意图,该行为有违诚信原则,扰乱网络直播秩序,违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侵害了消费者知情权等合法权益,最终判决驳回李某要求A公司支付直播礼物分成收益的诉求。李某不服提起上诉,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维持原判。
还有单身的赵先生在某视频平台结识美女主播“唯美”,“唯美”时常透露出想要上“千元榜”的心愿并请求赵先生帮忙打赏,面对赵先生“恋爱”的要求,“唯美”总是推脱、拒绝,最终还拉黑了赵先生。赵先生认为“唯美”欺骗自己感情涉嫌欺诈,起诉要求退还打赏并三倍赔偿。但北京四中院经审理认为,赵先生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具备相应辨别能力和认知水平,对“唯美”要求打赏的目的明知,不存在欺诈行为,最终驳回了赵先生退还打赏金额并三倍赔偿的请求。这两个案例充分表明,在基于欺诈或重大误解的直播打赏纠纷中,法院会综合考量多方面因素,关键在于判断是否存在欺诈行为以及打赏人是否存在重大误解,且打赏人承担着举证责任。比如主播故意夸大自己的悲惨遭遇诱导观众打赏,或者打赏人误将高额打赏金额看成小额金额等情况,都需要有充分证据才能得到法院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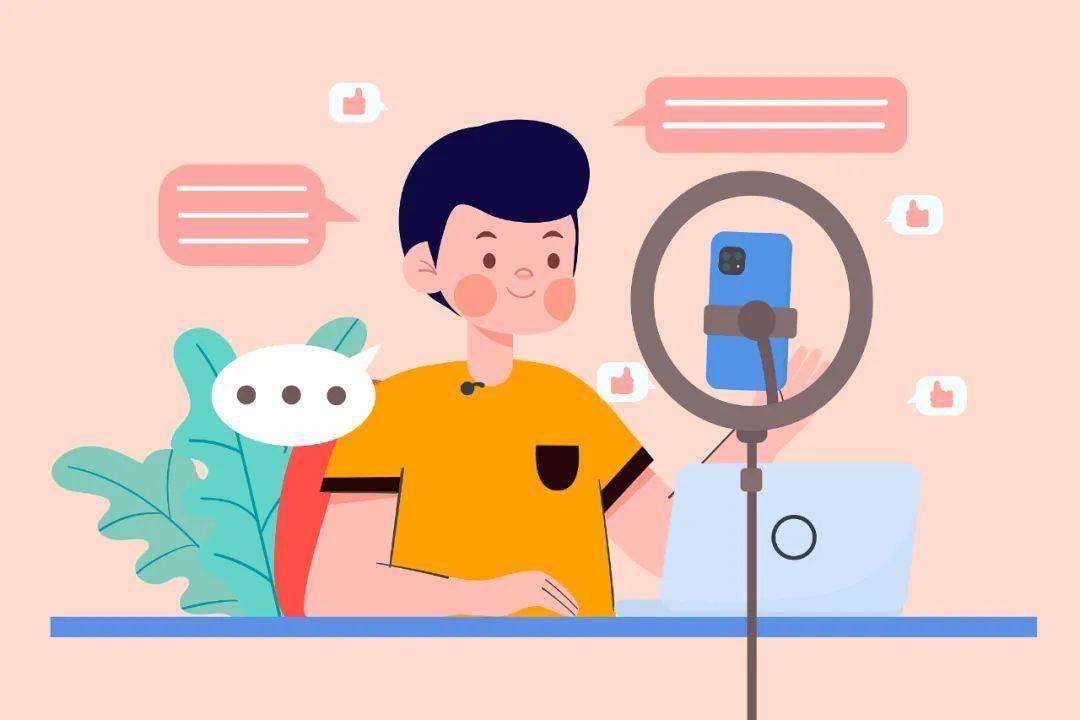
三、明确直播打赏法律性质与撤销权的意义
将直播打赏行为的法律性质界定为赠与合同,并明确在特定情况下打赏者可行使撤销权,具有多方面的重大意义。从解决纠纷的角度来看,这为处理直播打赏相关纠纷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有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减少不必要的争议和矛盾。从行业发展的角度出发,这有助于规范直播行业的交易秩序,推动直播行业在法治轨道上健康、有序地发展。通过对直播打赏行为的法律规制,可以引导主播合法合规地进行直播,避免诱导打赏等不良行为,从而营造一个良好的网络直播环境。
直播打赏行为的法律性质及其撤销权的行使是紧密相关且值得深入探讨的法律议题。随着直播行业的持续发展,相关的法律问题可能会不断出现,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的探索,以便更好地适应新的形势和需求。
撰稿人:星秩序律师刘会






